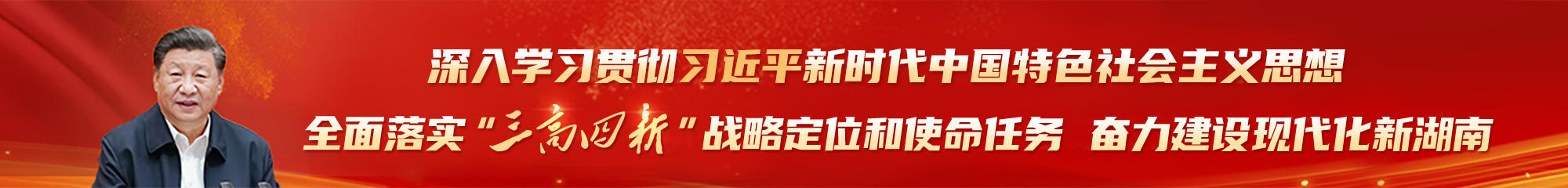|
“民意”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舆论,但其内核则是民心。唐宋时期,统治阶层对“民意”相对较为宽容,学者也多意识到“民意”同样为民本的重要内容。唐太宗曾撰《民可畏论》,“民可畏”也成为当时较为流行的思想。唐初学者成玄英亦认为:“不能爱重黎元,方欲轻蔑其用,欲不颠覆,其可得乎!”强调多数人的意志是国家政权的基础。柳宗元甚至有“受命不于天,于其人”之说,即君主合法性归根结底来自“民意”,而非“天命”。
入宋以后,随着学术下移,宋儒对“民意”更为重视,并将其作为约束君权的有力武器。宋儒领袖程颢、程颐进一步阐发了先秦民本中“民可近,不可下”的理论,在此基础上,“二程”提出为政之道,当“以顺民心为本”“以厚民生为本”“以安而不扰为本”。民心向背,是政权是否稳固的基础。理学集大成者南宋朱熹也提出:“丘民,田野之民,至微贱也。然得其心,则天下归之。”
对“君责”的思考。唐宋士人在延续“民为国本”的同时,更倾向于思考君主的本质。唐宋学者多认为,君为私而民为公,而民则是天的实体化。“君责”的基本理念直接影响了贞观时期的国家治理方略,由唐太宗亲自编撰的《帝范》就是在民本理念下向后世君主集中论述“君责”的典型文本。 |